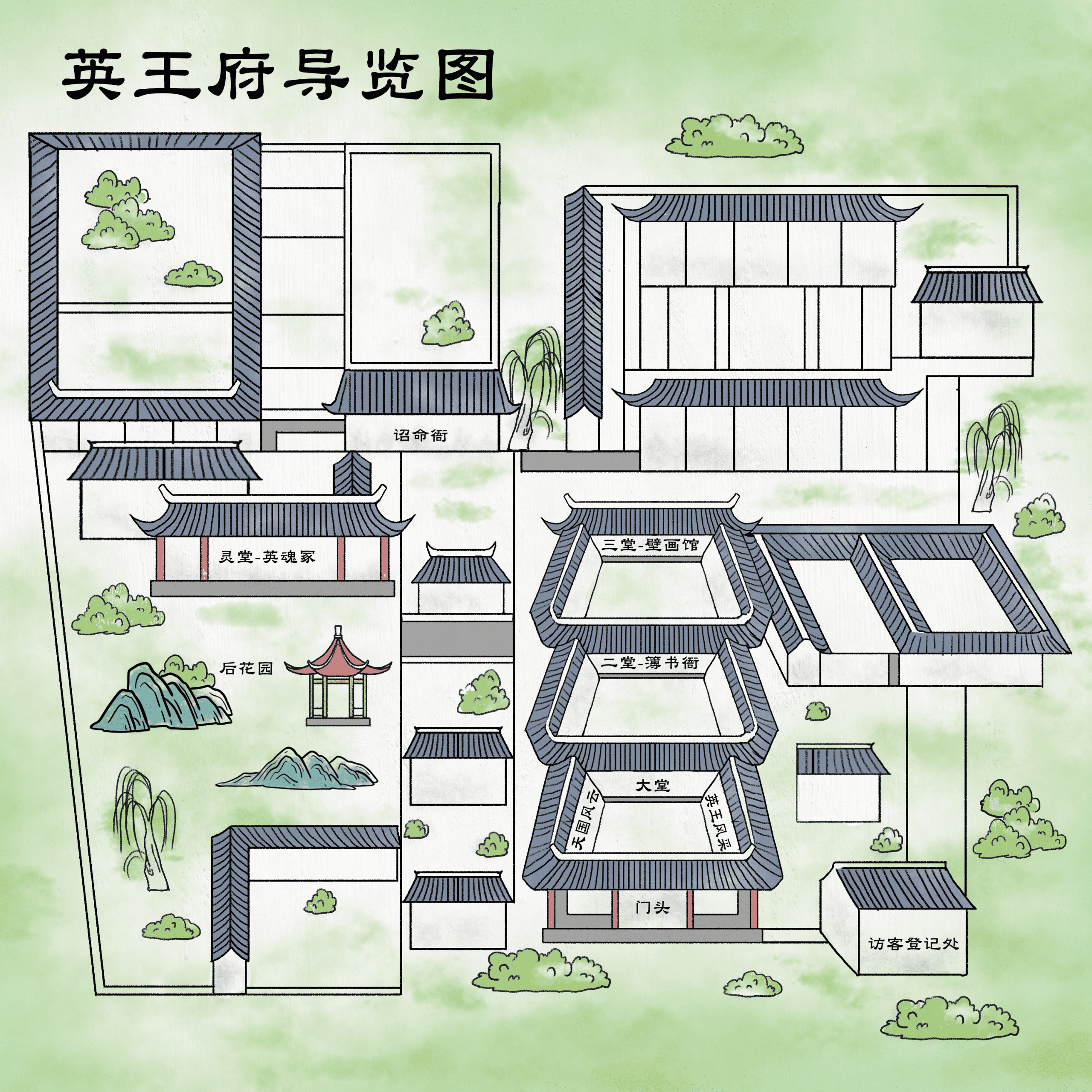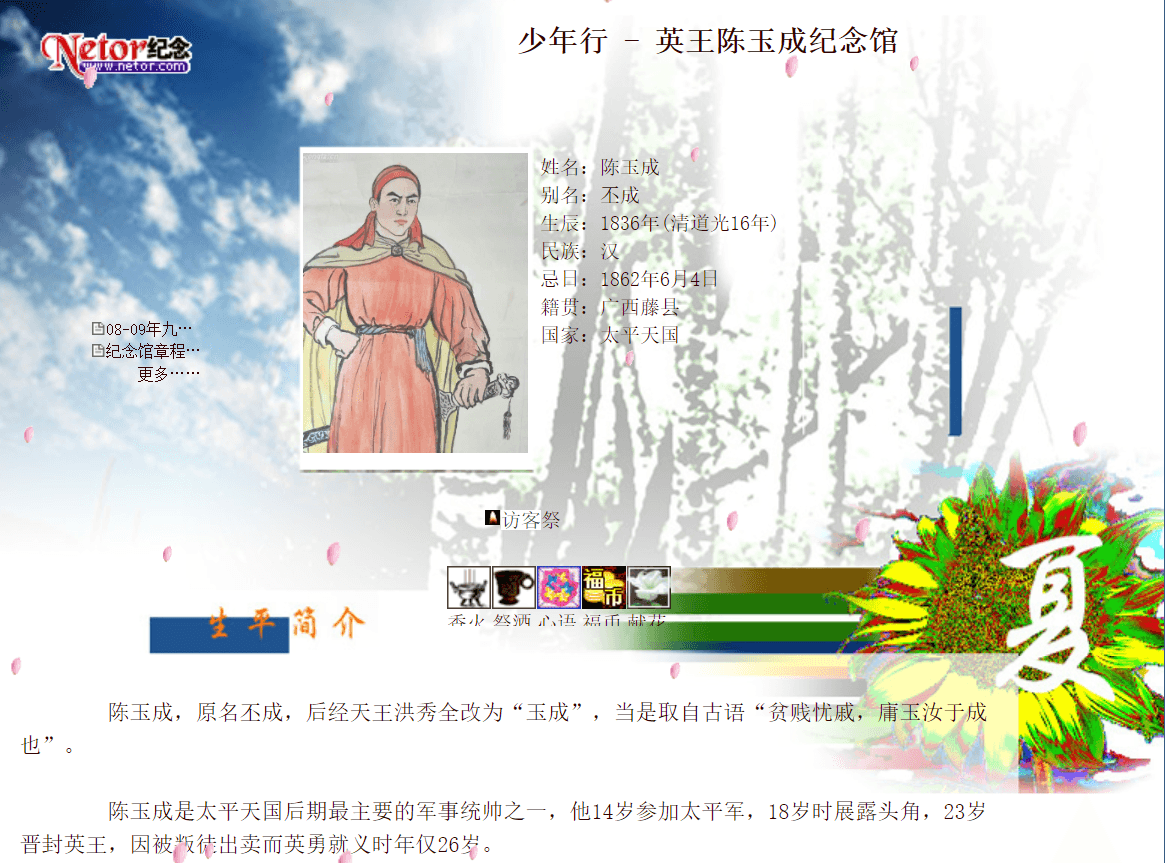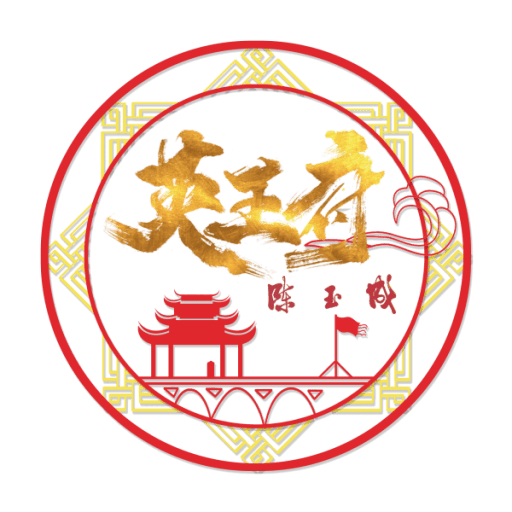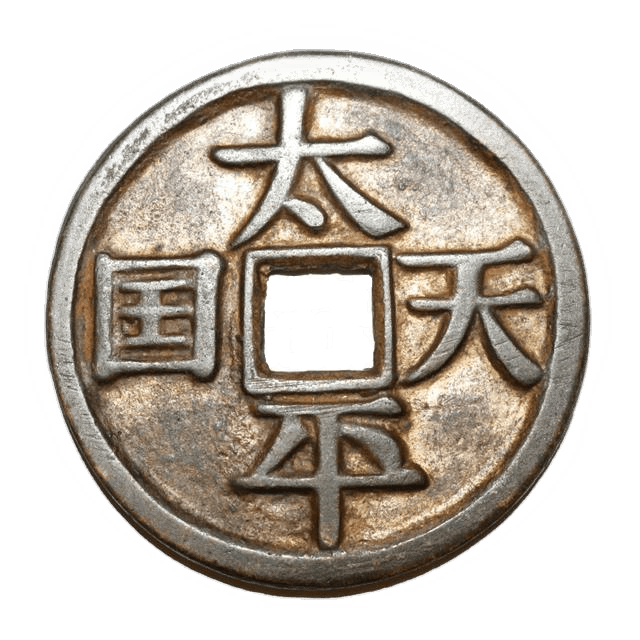陈玉成的生年
作者:苏三
陈玉成生年的传统说法是1837年(道光十七年),但以现有史料,最准确的说法是陈的出生落在1837年至1838年(道光十七年至十八年)这个区间,无法确定具体年份。当然1837和1838区别不大,这点误差大可忽略不计。本文只是谈谈传统说法的逻辑缺陷,以及为何陈的生年无法准确定位。
说明:当时的年龄算法是虚岁,所以陈的年龄记载我都减了一岁。
首先,能直接推定陈年龄的史料其实只有两处。一处是陈供词“十四岁(13周岁)从洪秀全为逆”,另一处是成书于1855年的《贼情汇纂》,“年十九岁(18周岁)”。陈并非没有其他年龄记载,但那些记载大多没意义,要么是道听途说,要么是随口编的(比如1861年陈和巴夏礼胡诌“我今年二十岁”)。
既然陈在“十四岁(13周岁)从洪秀全为逆”,那么原则上只要确认陈什么时候“从逆”,就能推算生年。问题在于,陈没有说清楚“从逆”指什么,洗礼入教?组织备战?还是正式起兵造反?罗尔纲将“从逆”解释成金田起义。金田团营在道光三十年(1850 年),起义在咸丰元年初(1851 年)。如果“从逆”指1850年到金田参加团营,那么陈的生年的确是1837年,这和《贼情汇纂》提到的1855年“年十九岁”也吻合。
但是,陈玉成是否真的参加过金田团营?拜上帝教在藤县的动员工作不算很成功,藤县信徒没有集体参加金田起义。直到1851年9月,萧朝贵等人到达藤县,当地拜上帝教信徒才被吸纳入营(详见《李秀成自述》)。照理来说,既然藤县其他人都没去,陈玉成作为未成年孩子,不可能一个人跑去金田“从逆”。为了解决这一矛盾,罗老师依据《贼情汇纂》,指出陈玉成是早期高层陈承瑢的侄子,所以他和藤县其他信徒不同,早早参加了金田团营。罗老师发表他的论证时,这套逻辑是自洽的。但是20世纪90年代,桂平县发现了陈承瑢家族墓碑,决定性地证明了陈承瑢和陈玉成不是亲戚,叔侄之说是《贼情汇纂》错记,换言之,陈玉成不可能跟着陈承瑢去金田,关于叔侄关系为何被证伪,详见一篇老文真假英王叔。
问题回到起点了,“十四岁从洪秀全为逆”究竟指什么?如果是指1851年9月萧朝贵收编藤县信徒,那么1851年9月时陈只有13周岁,则其生年是1838年。虽然1838年说无法和《贼情汇纂》的“年十九岁”对应,但既然《贼情汇纂》记错陈的身世,它关于陈的年龄记载就一定准确吗?年龄记载差出一两岁也不意外。例如《贼情汇纂》一边记下天京北王府对联“廿九岁月”,一边又说韦昌辉“年约三十余”,这其中就有一两岁误差原地。
另一方面,虽然陈玉成没参加金田起义,但“从逆”真的不能指金田起义吗?陈玉成在供词里自称“开朝元勋”,他编造自己参加金田起义不是很自然吗?有无可能1850年底金田团营时陈确实已满十四岁(13周岁),只是他没参加起义?
除此之外,《贼情汇纂》又说定都天京前陈年龄太小,“未与军事”,直到1853年才被封为典圣粮。太平军童子从牌尾转牌面的年龄是十五或十六岁(记载略有不同,十五和十六的说法都有)。如此看来,似乎1853年陈从牌尾转为牌面,也就是说当年陈满十五或十六岁(14或15周岁),则其生年是1838或1839年,再结合“十四岁从洪秀全为逆”,则可得出是1838年。但这种算法准确吗?太平天国是一个初创政权,很多制度是逐步完善的,我们能证明陈转正时已有严格年龄划分吗?有无可能1852年陈就满十六岁(15周岁)了,只是制度不完善乃至没转正?或者说,有无可能1852年陈已是牌面圣兵,但只是小兵,相关履历没被记入,以至于《贼情汇纂》错记成“未与军事”?《见闻录》记载陈当过罗大纲的近侍,这一经历不见于《贼情汇纂》。如果近侍职能包括侍卫,那么担任典圣粮前陈很可能已参加军事(不然空降典圣粮也不太合理),只是《贼情汇纂》没记。
总之,太平天国的原始史料严重缺失,很多事就是搞不清的,无法得出确凿结论。我在这篇随笔里提了很多小问题,它们都没有答案。我经常见人言之凿凿,一口咬定某事是怎样怎样,但实际上搞不清才是常态。
PS:我更喜欢1838的说法,因为那年是狗年